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南平军银锭的出现,说明了以今綦江南部东溪、赶水一带为中心的渝南黔北地区商品经济日趋发达,贵金属货币在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孤证不立,地下文物的出现又具有极大的偶然性,这是历史研究中最担心,也最无可奈何的问题。

▲志愿者深入南平军遗址一带开展田野调查。通讯员 陈正斌 摄
无独有偶,成立于2019年的,国内第一家以研究中国古代银锭为背景的专业学习平台——银锭博物馆,展示有南平军银锭一枚,铭文为“南平军发庆元三年夏季艮五十两,专库张智。庭。库官郭■,行人楹林■■”。再溯查该银锭,最早可见北京翰海拍卖有限公司在2011年以45万元价格成交的拍品,折合今制为1937克,介绍基本雷同。同行北京诚轩拍卖有限公司专业人员李晓萍在介绍该拍卖品时指出,该银锭为南宋精品。
据《庆元条法事类》卷三〇《上供》引“辇运令”规定:“诸上供金银,并以上色起发,内银销成锭(原注:大锭五十两,小锭二十五两,畸零凑数者听。如无上色去处,许用山泽),仍分明镌凿银数,排立字号、官吏职位姓名,用木匣封锁,于纲解内开说色额锭段数目字号。”宋元之际史学家胡三省著述的《通鉴释文辨误》也载,“今人冶银,大铤五十两,中铤半之,小铤又半之,世谓之铤银。”
李晓萍在《解密南宋金银货币》一文中也说,从现已出土的南宋上供银锭本身观察,铭文表述得非常完整,既有上供的州军府,税银的性质及重量,时间,排立字号,官吏职位,姓名等。结合本系列《流落成都的“綦江”宋代银锭(一)》可知,南平军庆元二年(1196年)、三年的这两枚银锭,不但重量与朝廷法令、同代文献完全吻合,且铭文与其它出土上供银锭要件基本一致。
只是拍卖公司判断庆元三年银锭为“福建南平军上供”,是混淆了古今地名差异,不了解宋代在今福建南平市先后设置的是邵武军、建宁军,而非南平军所致。
据《舆地纪胜》《宋史》等权威古籍记载,两宋有且只有一个南平军,是割渝州南川县(治在今重庆綦江)、涪州隆化县(治在今重庆南川),及播川城(治在今贵州遵义城区)等地新组合的一个跨今渝南黔北地区的州级行政机构,隶属夔州路(治在今重庆奉节)。
可见以上两枚银锭,出生地一定在南平军治所,即今綦江区东溪、赶水两镇交界一带。它们的出生时间仅隔一年,七八百年后相隔千里的两个不同收藏单位的专业辨识,信息来源不同,铭文中专业用词“发”“艮”“专库”“库官”“行人”完全相同,文序一致,小吏名讳也高度雷同,可证明它们皆是真品,绝非伪铸。
再结合两地信息,对比辨识这两枚南平军银锭图片文字,之前没有辨识完全或达成共识的古人名,现基本可确定为“专库张智”“库官邓坤有”“行人仝楹、林嵩。”

▲南平军庆元三年(1197年)银锭。通讯员 王洪林 翻拍
再回看南平军庆元二年银锭,铭文中确定了上解的白银性质是“经总艮”,其全称为“经总制钱”,是宋代杂税“经制钱”和“总制钱”的合称。据2002年第三期《中国钱币》收录的,李小萍撰《南宋“经总制银”银铤考》一文,钤(qiǎn)有“经总制银”铭文的银锭目前只发现五枚,除咱们南平军这枚外,另外的分别是1955年湖北黄石市西塞山出土的3枚,1975年河南方城县杨集出土的1枚。
经制钱始于北宋宣和四年(1122年),具体名目有权添酒钱、量添卖糟钱、人户典卖田宅增添牙税钱、官员等请奉头子钱、楼店务添收三分房钱等,涉及酒类买卖、土地交易、官员服务、商业场所租金收益等。
总制钱始于南宋绍兴五年(1135年),具体名目更为细微,计有转运司移用钱、勘合朱墨钱、出卖系官田舍钱、人户典卖田宅牛畜钱、进献贴纳钱、常平司七分钱、茶盐司袋息钱、装运司代发斛斗钱、免役一分宽剩钱等。
由以上名目繁多的税种观之,今东溪、赶水交界处鱼沱一带的大綦市,在南宋已经不限于官方垄断交易的锦马互市,更多的是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民间边贸。又为“綦走发现”2022年11月3日文中“在南宋后期,大綦市又因商品交易日趋繁荣而更名綦江镇”的观点提供了有力的间接证据。
经总制钱一部分属增税,一部分则属移用某些财政专款。本来是为了整顿和规范长江以南地区的财政收支而设立。但因为经总制钱岁无常入而有常额,一旦某项歉收,必然另外巧立名目补征,成了危害百姓的苛捐杂税。该银锭又从另一个角度为南宋“正税之外,科条繁多”增添了有力的直接物证。
根据出版《宋代银铤考》的学者刘翔《南宋“武冈军经总银”银铤解析》一文,在2013年,“经总制银”银锭家族又添加了两位新成员,即武冈军(今湖南省武冈市)淳佑十年(1250年)春季经总银、郴州(今湖南省郴州市)起解的经总银。
刘翔在上文中还明确,“发现的‘经总银’则以五十两的大铤为主,小铤反而鲜见。”可见南平军庆元二年这枚二十五两经总银,对研究南宋边区经济活动的文物价值,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在目前发现的南宋各州军上解的银锭中,还有的铭文非常简单,只有上供的州军府和上供银,且通常出现在砸有京销锭银、或临安、或总领所地名、银铺名戳记的银锭上。在《南宋“经总制银”银铤考》中,湖北黄石市西塞山出土的银锭,其中两枚铭文中就有“霸北街西口宅韩五郎”“铁线巷南朱二郎”一句。霸北街在今杭州市洋坝头附近,中山中路凤凰寺靠北。铁线巷在今杭州邮电路附近。韩五郞、朱二郎及另一枚铭文中的四郎,都是金银匠的名字。这些银锭是各州为了完成“国税”指标而在朝廷所在地临安或总领所的金银铺购买的。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曾任桂阳监的章侁(shēn)作诗云,“官中逐月催租税,不征谷粟只征银。”在商品流通闭塞,又不产银的地方,在兑换银两纳库的过程中,将承担额外的汇率成本,最终转嫁给老百姓。
显然,南平军的这两枚银锭皆不属此列,特别是庆元二年银锭长秤三十铢,南平军也不可惜(详见《流落成都的“綦江”宋代银锭(一)》文中解析)。这也佐证了当时的南平军税收状况良好,还不至于像其他地区那样,为了完成税收指标而打肿脸充胖子购买充数。从这个角度来看,当时的南平军民众不会因为“买银”而再次受到盘剥,日子相对好过。
两宋朝廷的白银来源,主要有坑冶,专卖品钞引买卖收入,各种食物及税收折银。根据渝南黔北地区并没有银矿的地质构成,说明南平军解送的白银应是在商品流通和消费服务环节的税费中聚集的。
宋代白银货币地位的上升,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跨区域交易的大宗商品买卖。而綦江区社科联2024年度调研项目鉴定结果(綦社联〔2024〕13号)公布的一类项目第一名,杨友钱先生牵头,“綦走发现”团队结题的《地名“綦江”的形成演变及位置变化》文中,明确了大綦市在南宋时已成为了朝廷与土著族群互市的全国性八大市场之一,是边贸“特区”。显然,白银作为价值稳定的货币,是大綦市经贸交流很常见的硬通货。
又从“綦走发现”2022年11月10日文中依据南宋《舆地纪胜》记载论证的“取铁铸钱,织锦制茶”部分了解到,南平军自元丰二年(1079年)起设置有专门的铸钱监——广惠监,至绍熙末(1194年)才停铸,时间跨度长达115年,说明南平军拥有过硬的专业铸造技术人才,为南平军庆元二年、三年两枚银锭一定出自“綦江”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又进一步印证了“綦走发现”有关大綦市经贸繁荣的观点。
(未完待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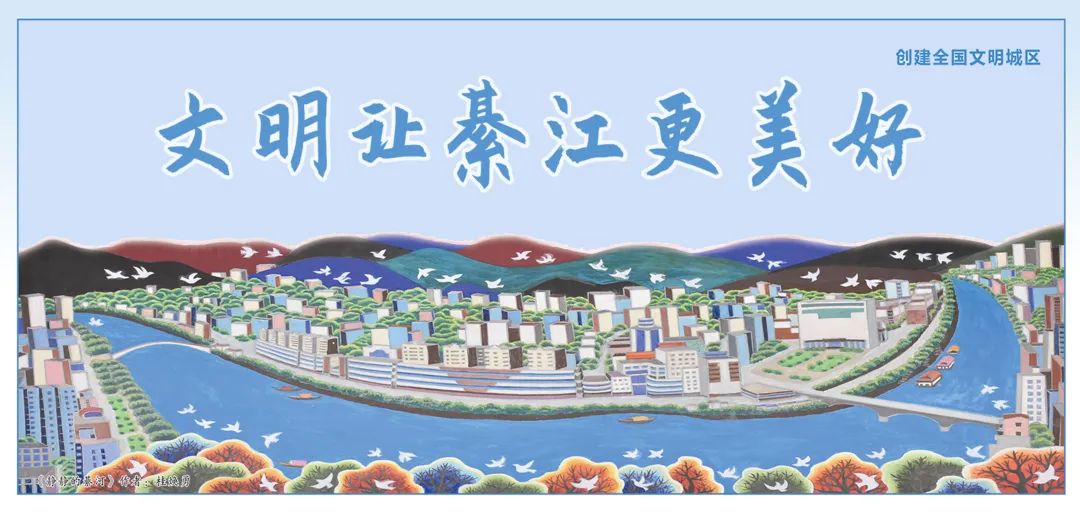

编辑:胡雪妮丨责编:马 卓 肖健忠
编审:马小玲戴 航
监制:赵 新孙 萍
END
来源:綦江日报丨通讯员 王洪林(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
@綦江文旅体
